编者按:法国大革命之后,从君主立宪制、共和制、革命专政、帝国、王朝复辟,政体不断变化。大革命之后什么才是法国?即“自法国大革命这一基本事件以来民族特性是如何构建的?”就成为莫娜·奥祖夫“革命·文学·女性三部曲”的核心问题意识。本文梳理了三部曲之一《女性的话语》中不同时段的法国女性的生命经历和个性、观念,从她们或坚持信仰,或在新旧之间挣扎,或彰显女性权利,或寻求两性对话等丰富多元的思想特征,来认识法兰西社会本身含混多重的性格。
《法兰西的女性世界》
文 | 王英(《读书》2022年9期新刊)
“女性的画像属于一种男性题材。它鲜有出自女性之手,也极少关心她们的话语。”奥祖夫在《女性的话语:论法国的独特性》中开宗明义,她要改变龚古尔兄弟、米什莱这些男性史学家笔下那些刻板的女性模本,大量女性研究似乎都更倾向于规定女性的角色和义务,确定女性形象的规范和标准,对不符合典范的部分加以修改、擦拭和模糊处理,而不关注她们自身的说法和道理,倾听她们自己的声音。或许作为女性学者,奥祖夫更有能力和意愿诠释女性这一含蓄而又意味深长的存在,对她们的命运给予更具同情性的理解。

奥祖夫并未令人失望,她如同一个高明的猎手,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和档案中,拣选出法国历史上十位女性来探索她们的世界,通过书信、小说、回忆录和政论文章的梳理和重构,描画出一幅幅风格各异的图像,令那些逝去的人物容貌和灵魂宛若新生。她也如同一个优秀的摄影师,在最能展现人物特点的那一刻按下快门,捕捉到每一个人最为幽深微妙的那一面:玛丽的固定不变、玛侬的英勇无畏、热尔曼的焦虑不安、奥罗尔的宽宏大度、于贝蒂娜的执拗、加布里埃尔的贪婪、西蒙娜的渴望。经过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两百多年的巡礼,法国女性世界如同巨幅画卷逐渐铺陈开来,最终这一画卷超越了性别的含义,如同湍急的支流汇入大海,而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象征。
一、从旧制度到大革命
哈贝马斯曾经盛赞欧洲的沙龙文化,“在妇女主持的沙龙里,无论是贵族的,还是平民的,亲王、伯爵子弟和钟表匠、小商人子弟互相来往,沙龙里的杰出人物不再是替其庇护人效力,意见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”。十七、十八世纪的法国沙龙是时代思想和风尚的引领者、公共生活的象征,沙龙女主人学识丰富,精通拉丁文、哲学、历史、几何学、物理和化学等,这里性别、等级、阶层、国界都变得不再重要,只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则都可以进入。迪·德芳夫人玛丽就是沙龙女主人的典范,她每天下午接待圈中密友,尽可能长久地留住身边的簇拥者,达朗贝尔和伏尔泰都是她沙龙的座上宾。她和伏尔泰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和通信,交换着关于信仰、理性、品味等诸多事物的意见。伏尔泰深信启蒙能够战胜蒙昧和愚昧,而玛丽则判定伏尔泰将他的才华浪费在反对教权的斗争,她相信皈依宗教有着积极意义,有信仰的人生才是最为稳妥的人生。晚年她已经双目失明,但去世前几天里还兴奋地记录着宾客的人数、收到的信件,操心安排晚餐。玛丽博学多才,拥有确定的判断力,容忍自身的脆弱和缺陷,她或许抱怨人类普遍的不幸和悲惨境遇,却从不认为作为女性有什么特殊的制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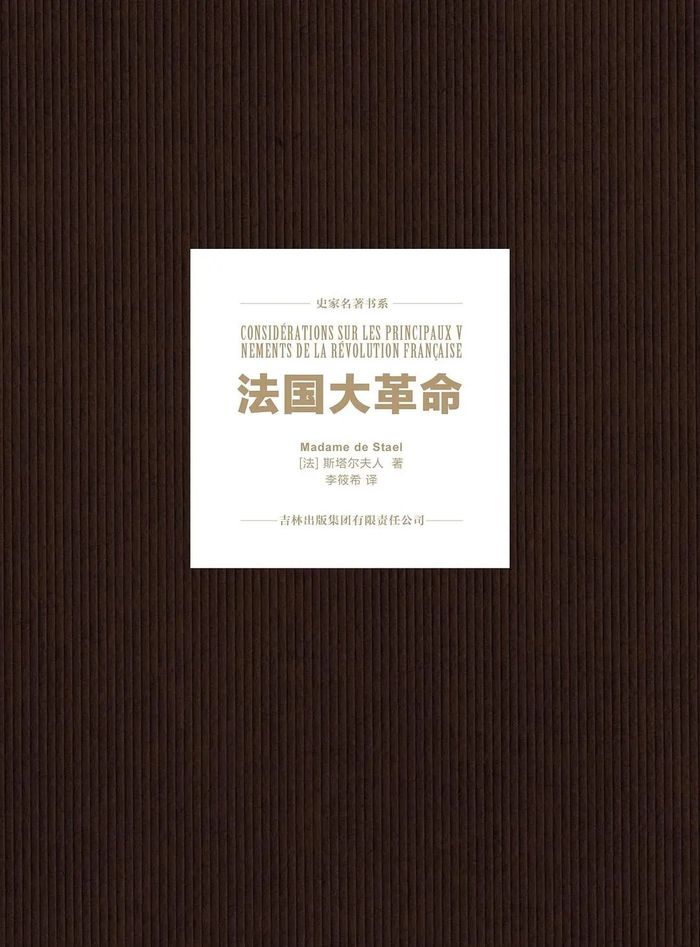
玛丽在一七八〇年告别人世,旧时代也在几年之后戛然而止。奥祖夫书中选择的四位女性都或多或少地卷入法国大革命的风暴,德·沙里埃夫人、德·雷米萨夫人、罗兰夫人,特别是斯塔尔夫人,她丰富的政治论文和文学作品,构筑了革命时代女性生存丰富而矛盾的蓝本。作为路易十六财政大臣内克尔之女,斯塔尔夫人直接卷入到大革命风起云涌的上层权力博弈中,一七九五年她完成了《论国内和平》,试图对大革命之后法国秩序重建给出自己的解释,她反对保皇党复辟旧制度的企图,也反感雅各宾派过于激进化的革命,认为人们不应该被狂热革命的激情裹挟,各派力量应该谋求一个温和、理性的立宪政府,宽容并善于妥协是利益政见不同的派别能够协商的重要品质,也是危机重重的法兰西获得秩序的必要条件。经过和父亲内克尔深入讨论和广泛阅读,斯塔尔夫人在一七九八年完成了《论当前形势下如何结束革命和巩固共和国》,尝试从英国宪政中寻求灵感,帮助热月党人完成了较为中庸和具妥协色彩的共和国宪政设计。
那么大革命带给女性的命运怎样?对于雅各宾派而言,只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感情,那就是对共和国的爱,为了公众利益和祖国可以毫不留情地牺牲一切,包括妇女们对家庭的兴趣、私人情感和宗教信仰。斯塔尔夫人意识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变化,《论法国大革命的主要事件》中,她清楚表明革命对女性的不友好,启蒙时代妇女主持的沙龙已经被革命会议杀死,旧制度下的性别混杂等同于无秩序、堕落和阴谋,女性曾经拥有的生存空间被革命逐渐侵蚀。《对玛丽-安托瓦内特的辩护》中,斯塔尔夫人确定无疑地指出,革命铸就了一个恐怖时代,其残酷凶狠给了女性致命一击,玛丽王后走上断头台,所有女性都与这位美丽温柔的母亲一起遭到杀害。雅各宾派在女性身上看到的是天生的反叛者和敌人,其做法是将私人领域公共化,将家庭纳入革命范畴之中,妇女们获得自己的价值,但是仅仅是作为公民的妻子或母亲。大革命带来的两性之间的隔阂影响了未来一个世纪,女性主持的沙龙销声匿迹,女人成为反动天主教会的支柱,藏匿教士并庇护暗中举行的弥撒,她们被排斥在选举权之外,成为共和国不值得信任的人。

对斯塔尔夫人来说,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,旧制度下仪表、风度、信仰和生存模式已经渐趋消亡,政治和性别平等的新时代还是遥不可及的远景。一八〇二年之后,在被拿破仑强制流放的岁月里,她创作了一系列以女性命运为中心的小说,《黛儿菲娜》或者《柯丽娜》的女主人公都有着法国数学家索菲·热尔曼的影子,她们一生都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之中挣扎,也一生都摇摆于荣誉和爱情之间,她们为发展自己的天分辩护,但是享有自由意味着承受世俗偏见、政治打击和无尽孤独,无论斯塔尔夫人还是她的女主人公们都付出了巨大代价,其悲剧性的声音穿过大革命的厚重雾霭,依然回响于法兰西的天空。
二、十九世纪的侧影
以赛亚·伯林曾经就思想家、作家和各类知识分子的气质做过一个分类:一边的人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见识,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,他们将一切归纳于一个单一普遍的原则,他们的人、他们的言论,必唯有本此原则才有意义;另一边的人追逐许多目的,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联,甚至经常彼此矛盾,他们的生活、行动与观念是离心的而不是向心式的。前一种思想人格和艺术人格属于刺猬,后一种属于狐狸,这项研究后来转化成耳熟能详的谚语,“狐狸多知,而刺猬有一大知”。法国十九世纪女性世界便是这两种气质类型的混合,最能成为这个世纪写照的则是老狐狸乔治·桑和大刺猬于贝蒂娜。

乔治·桑毫无顾忌地认同自己的女性气质,“我同其他女性一样,体弱多病,骄躁易怒,充满幻想,极易感动,并且作为母亲无谓地担心”;她毫不犹豫地承认甘愿为了爱情而服从,她借小说《印第安娜》主人公之口说出,“控制我,我的血液,我的生命,我的整个身心都属于你。带我走吧,我是你的财产,你是我的主人”;她将母性情感定义为女性最独特之处并为此而骄傲,甚至在她与缪塞、肖邦的两段恋情中,她都会将情人像孩子一般地疼爱和照顾。但如果将她的形象固定为脆弱服从的女性,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,没有谁比乔治·桑更不愿意将自己固定为某种“特定的模式”,她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不断变化外形,让你迷惑于她到底是谁,她穿戴着男式西装、宽大的领带和灰色帽子,踏着黑色长筒靴走在巴黎街道,口中叼着雪茄和烟斗,自我指称时随意使用阳性和阴性,还有着男性化的名字“乔治”,她独自住在巴黎过着和男性一样的创作生活。缪塞称她为“我所认识的最女性化的女性”,而她则跟朋友说,“把我当成男人或女人,悉听尊便”。
乔治·桑的“狐狸属性”,她的含混性、矛盾性和多重性体现在诸多方面,她的祖母是波兰王室的后裔,而母亲是一个普通鸟商的女儿,她在祖母庄园长大并接受贵族式教育,成长过程中却被母亲的浪漫主义民主理想所打动。一八四八年她站在民主派一边,创办了革命派的报纸,撰写文章支持“二月革命”,但她完全禁止儿子莫里斯参与街垒活动。她对于女性主义运动亦持调和的态度,相信人类种族和性别上的平等,支持妇女争取自己的权益,但在乔治看来,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做法是本末倒置,也是一个仓促的错误,如果妇女都没有在婚姻中获得独立,取得受教育、财产和离婚的平等权利,又怎么指望她们代表人民参与政治事务?一八四八年“六月革命”的失败更让她看清楚了这一点,人类事务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,过于超前的政治诉求会带来更大的伤害,要学习妥协、等待和循序渐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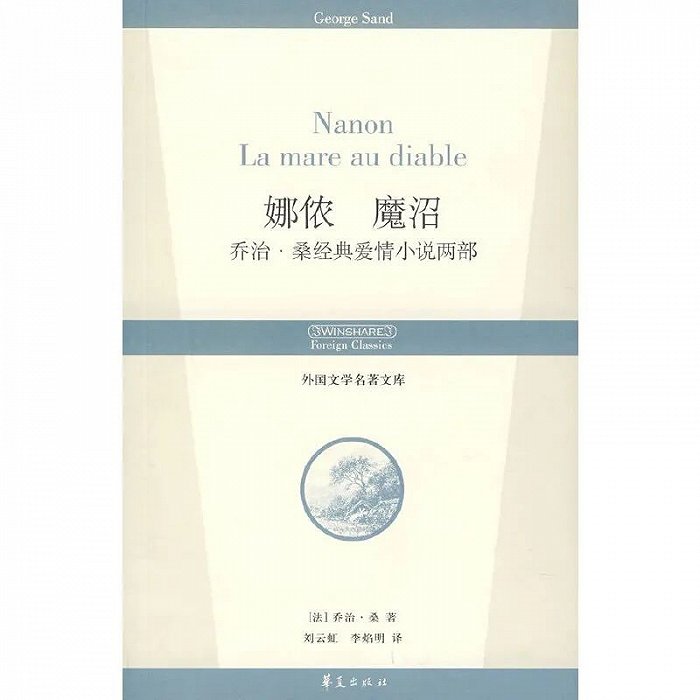
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,乔治·桑回到了贝里,在隐居和创作中度过晚年。同一年于贝蒂娜出生在阿列省一个共和主义家庭。她二十四岁移居巴黎,从一个简朴的套房搬到另一个,墙上始终挂着乔治·桑的画像,然而她和变化多端的乔治实在是精神气质的两个类型,她拥有一种狂热的一元识见,是毫无疑问的“刺猬属性”。于贝蒂娜在二十岁左右思想就奇特地定型,她心中有一个不可动摇的神圣形象:女公民和女选民,终其一生都是为这个固定信仰而奋斗,经历无数痛苦而百折不挠。她争取妇女政治权利有几种主要手段:给参议院、众议院、部长、将军、大臣、作家们写信和申辩;收集签名和请愿,参加游行甚至卷入暴力示威活动,到大街、广场、市政厅要求将女性登记为选民;创建自己的机关报,她创刊了《女公民》并且撰写了大量文章,反复重申同样的主题。为了女性公民选举权,于贝蒂娜忍受了逮捕、查禁、贫穷、独身、爱人的死亡,她牺牲一切、付出一切,乃至于开罪一切,甚至不惜和共和主义的敌手联盟,和保皇党、反革命的教士或激进社会主义者结盟,战斗的生活使她四处树敌备受侮辱,执拗不讨好的性格更加深了她的孤独。
法兰西的十九世纪是动荡岁月,帝制和共和如拉锯一般来回撕扯,不同集团、阶层乃至性别之间都弥漫着浓厚的敌意,革命浪潮此起彼伏,稍有不慎就会剑拔弩张硝烟弥漫,因为乔治·桑,这个世纪的侧影稍微带上了一丝宽厚和温情。十九世纪也是一个缓慢变化转折的时代,女性逐渐在家庭、教育、政治等方面获得平等权利,幸亏有了于贝蒂娜,一向被漠视的女性在商店、工厂和车间开始赢得微不足道的权利,选票也成为她们保护自己的一个途径。
三、在科莱特和波伏娃之间
一九五四年科莱特去世,教会拒绝为她举行天主教葬礼,然而法兰西共和国接纳了自己的女儿,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科莱特有一系列令人目眩的标签:大作家、同性恋者、脱衣舞女演员、法兰西时尚代言人。但女性这个身份对科莱特具有决定意义,她拒绝模仿男人的形象,不断抗议时代将男性化角色强加给女性,自由意味着对于女性禀赋的接受、深化和赞美,自由在于坚持不懈地成为自己,回归女性的使命和天赋。科莱特的生活和作品中,女性都是更有智慧和力量的存在。在《流浪女伶》《桎梏》《麦苗》《葡萄卷须》这些小说里,科莱特沉溺于描绘那些拥有力量感的女人。这些女性拥有男性所没有的胆量、勇气,面对不幸有非凡的抵抗能力,她们还拥有不放过任何人尤其不放过自己的无情目光,毫无粉饰地评估世界、贪婪和计算的能力,女商人一样的精明和诚实。而她小说里的男性呢?其才能微不足道,平庸而脆弱,经常因为无足轻重的挫折就倒下了。科莱特作品如此,生活亦如是。她的父亲是一个沉湎于幻想的退伍军人,做着不切实际的文学梦,却没有在本子上写下一个字,而母亲茜朵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典范,为自己和孩子们建造了一个坚固的生活堡垒;她的丈夫威利窃取了妻子的小说署上自己名字,这桩丑闻最终以离婚而告终,而科莱特一生中最真挚的爱情给予了贝尔伯爵夫人米茜,虽因世俗压力被迫分离,但终其一生科莱特作品里女同性恋的爱情总有着不同寻常的深情,带给人别处没有的纯粹和安全感。

背对宏大,面向近处。远离荒谬而混乱的政治世界,女性的智慧就在于迅速回收被周围灾难摧毁的生活碎片并重建家园,科莱特的小说里弥漫着巧克力和金雀花的香味,有着飘飞的长方形小果实,花园里色彩斑斓的蜥蜴,镶嵌着米粒大珊瑚珠的耳环,关注并描绘这些微观、富有生活气息的感性事物,在她看来是女性追求自身完整性的一种方式,也是在混乱而不完美世界中自我救赎的永恒法则。就在科莱特去世的一九五四年,西蒙娜·波伏娃女士获得了法兰西龚古尔文学奖,她和科莱特反向而行,最终殊途而同归。西蒙娜从不关心动物、植物和小饰品,她接受了和男性相同的教育,二十几岁就取得了和男性一样的成绩和经济独立。对西蒙娜而言,完整性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入男性世界,平等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并取得同等成就。西蒙娜介入了她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智力创新和政治活动,成为一个和萨特并驾齐驱的存在主义领袖、一个知识分子,她也参与了时代波澜壮阔的政治实践,是欧洲左翼政治运动的先锋、共产主义的同路人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支持者。忽略琐屑,拥抱宏伟,她是一个永不疲倦的广阔世界的探索者和开拓者。

四十岁之前,女性身份对西蒙娜来说毫无意义,每个人都要面对疾病、命运的变幻莫测,每个人都要扛下艰难的工作和生活,男人和女人并无区别。女性的发现和《第二性》的写作对西蒙娜来说是一个偶然,国家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资料将她骤然抛进一个女性世界,一个她身在其中而不自知的世界,而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,性别构成了她们命运的底色,甚至是她们的全部。《第二性》把西蒙娜·波伏娃推到风口浪尖上,她得到几乎等量的荣誉与辱骂,信任和怀疑。一方面她揭露女性的屈从地位、社会性的奴役和压迫,被推选为妇女解放的旗手,成为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者;另一方面西蒙娜竭尽所能地抗拒两性之间无法沟通的观念,也不愿意接受性别之间完全敌对的假设,激进女性主义者则怀疑她的态度,辱骂她的虚伪和两面派。西蒙娜始终会做出自己的选择,她珍视性别之间的难能可贵的关系,就像她和萨特一样,自然、轻松、有竞争合作,或许爱恨交织而最终不失诚意的关系,她始终没有采用美国式的攻击性腔调,而保留了适度的节制和温和,这是波伏娃本人的选择,也可以看作法国女性主义运动始终都比较温和的一个标志。
四、在女性世界寻找多元
一个国家就像一条船,在漫无边际几乎静止不动的水面航行,水面之下便是悠久的历史和文化,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变化多端。波澜不惊的文化河流承载了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这条大船,也决定了法国何以为法国。年鉴学派的前辈布罗代尔在《法兰西的特性》导言中指出:“虽然过去和现在被丘陵、山脉、断裂和差异等障碍物所隔开,但过去终究经由大道、小路乃至通过渗透而与现在相汇合: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过去在我们周围漂浮。”他搜索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过去,追逐那些起落不定的潮水,探寻那些来自历史深层的泉涌,判断它们怎样像江河汇入大海一样融入现实。奥祖夫遵循着布罗代尔的教诲,她拓宽了丈量历史的时间尺度,得以搜索法国女性文化的丰富和多元,观测两百多年间迥异的生存故事和生命意义如何汇入当下。《女性的话语》里奥祖夫展现她捕捉多元价值和多种人类命运的能力,观察主人公各自不同的性情、观念和举止,不厌其烦地倾听那些语气和音色大不相同、意味深长的私语,陪伴她们感受生存的快慰与艰辛、命运的幸福或悲戚。这些丰富多样的声音和女性画像构建了法兰西的民族记忆,也不经意间缓解了现代女性主义的极端倾向,并塑造了法国的独特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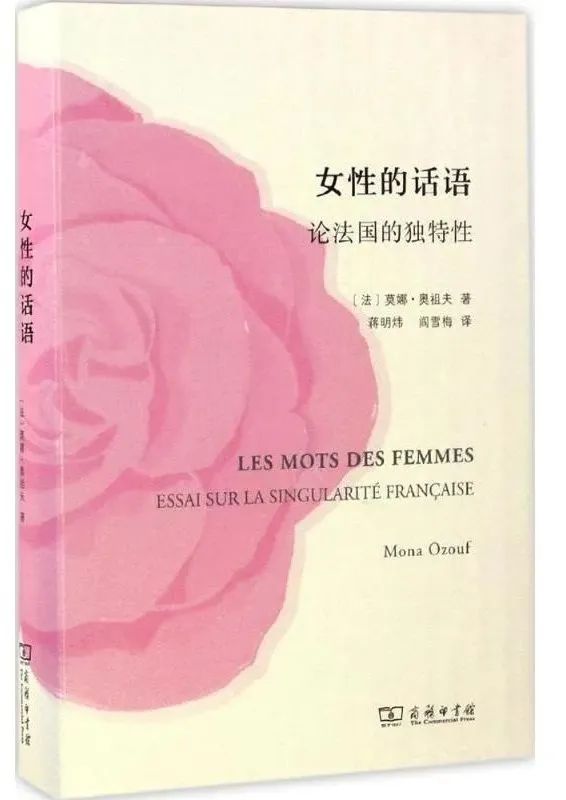
在源远流长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所带来的震荡之间,奥祖夫一直在寻找一条和解之路,她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法兰西“自法国大革命这一基本事件以来民族特性是如何构建的”,而革命·文学·女性三部曲正是她探索法兰西民族特性的尝试。在奥祖夫看来,法兰西的特性存在于两个相反相成的特征之中,《革命的节日》展现了法兰西特性的一方面,“人们是通过革命者的意志主义教育学,通过消除相异事务的热火朝天的热情来进行这种建构的”,法兰西致力于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,建构一个统一的认同,用革命热情统摄和取代一切;《小说鉴史》和《女性的话语》则探索法兰西特性的另外一方面,“人们反其道而行之,通过抵制这种事业来从事这种建构”,妇女和文学所扮演的角色,指向对于多样性的寻求。大革命并没有将女性变成千篇一律的爱国者,而是各自有着鲜明的形象:执拗或灵活、庸俗乏味或富有创意、宽宏大度或独断专行、拥抱整个世界或将世界圈入设定的界限。奥祖夫深知正是在她们身上,蕴含了一个更真实,或许更会流传久远的法兰西,就像是十三世纪法国寓言长诗《玫瑰传奇》中的形象,优雅鲜明并饱含着敌对的美德。
来源:读书杂志



评论